某個被偷走了賴以為生的鍋而歇斯底里痛哭的女人,一夜之間突然消失的15萬難民,被拋棄在街頭等死的童軍,火車飛馳而過的最后一秒抓起攤位上一切能抓住的東西拔腿就跑的人們……
在漫游、觀察非洲30多年后,傳奇記者雷沙德·卡普希欽斯基在《太陽的陰影》中記錄的這些故事,是書中讓人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卻遠遠不是全部。他還寫下了非洲那些不為外界所知的大屠殺、普遍的饑荒、兒童戰爭、不知何謂統治的統治者……他始終在嘗試抵達、傳達非洲的內核,那個口述歷史、信奉祖先與神靈、擁有勻速旋轉的永恒時間的世界。

“《太陽的陰影》呈現了歷史與現實不斷對話、神話與現實互相交織的鮮活世界。它帶我們進入的這趟旅程并不輕松。”譯者毛蕊說,正是那些殘酷、直擊歷史、直擊現實的甚至讓人不寒而栗的片段,讓她在刻板印象的裂縫中,觸摸到了這片真實的大地,重新認識了非洲。
8月15日,第一財經年中人文書單在上海書展發布,《太陽的陰影》獲評年中十佳好書。評委會認為:“只有雷沙德·卡普希欽斯基,能寫出這樣一個裸露、洶涌、真實到殘酷的非洲。”由波蘭語直譯的這部作品,將優美生動的描寫與干凈有力的新聞語言結合,譯作精準傳達了卡普希欽斯基的紀實風格與悲憫情懷。
毛蕊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俄羅斯東歐中亞學院波蘭語專業負責人,也是國內僅有的六位波蘭語博士之一。自2021年以來,毛蕊每年有譯作問世,包括科幻作品《機器人大師》、自然文學作品《抓住十二只喜鵲的尾巴》、傳記《辛波斯卡:詩心獨具的私密傳記》、紀實作品《太陽的陰影》等。她形容翻譯的過程就像在夜空中看到璀璨的流星,“但怎樣把流星的美傳遞出去,讓讀者也有同樣的感受?”經歷這個艱難的過程,她找到了、傳達了,內心會有持久的滿足感,這正是學習語言、翻譯帶給她的美好。

第一財經:《太陽的陰影》是一本非常有力量的書,作為譯者,你有什么閱讀或者翻譯的感受想傳達給讀者?
毛蕊:在我看過、翻譯過這本書之后,覺得自己之前對非洲的認知是非常狹隘且淺薄的。除了熱、沙漠、動物大遷徙等,就沒什么印象了。所以看完這本書的最大感受就是,我對世界的認識太少了,而對自己的關注可能過度了。所以我真誠地向每一個關注這個世界、關注其他命運個體的人推薦這本書。
閱讀之后,我知道了很多不僅新鮮,甚至很難理解的觀念。比如說“時間”,卡普希欽斯基寫道,非洲人對時間的觀念和歐洲人不一樣。在這點上,我們亞洲人和歐洲人是統一觀念的,認為人受時間的制約,人與時間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沖突,而且這場沖突永遠以人類的失敗告終。但非洲人認為,人類在影響時間的形成。時間是由事件的發展呈現的,而事件是否出現,取決于人,時間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只有人參與了、事情發生了,時間才存在。
宗教和神靈的力量在他們的生活中大到難以想象。人類的活動要首先得到祖先和神明的允許;人死去后,會被埋在家里,通過這種方式繼續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另一個讓我覺得震撼、悲涼的事實是,非洲的死亡都是“復數”的,都是集體性的,都是大規模死亡的。
在書的結尾,卡普希欽斯基描述了一次與大象的眼神對視。他描寫得太生動了,讓我能感到大象的眼神是如此有神、有力量的一種目光,以至于我現在看到大象的圖片會一種有不寒而栗的壓迫感。之前我對大象的印象是溫和的、笨重的,在動物園的圍欄里慢慢地啃著干草。現在當我再說出“動物園里的大象”這句話,已經感覺到這是一種折磨了,而動物園里的大象永遠也不會有卡普希欽斯基描寫的這種眼神和精神。
第一財經:這樣一個非洲,可能對大多數人是非常陌生、遙遠的。
毛蕊:卡普希欽斯基描述的是四五十年前發生在非洲大陸的故事。雖然時空相隔遙遠,我們對這片大陸也所知甚少,但我們讀的時候并沒有陌生感,也沒有時代變遷帶來的隔閡感。我們今天依然對所謂的“南方”關注非常少,但是卡普希欽斯基提醒我們,真正處于少數的其實是“北方世界”,生活在溫暖氣候中的人口才是世界的大多數。
書里講到好幾場戰爭、屠殺,而我們對此幾乎一無所知。包括現在,南蘇丹依然飽受暴力沖突困擾,但幾乎也沒有人關注。大家都在關注“北方世界”,其實北方世界的中心就是白人中心。
書中記錄了這樣一個片段:有一天卡普希欽斯基聽見一聲絕望的哀嚎,一個女人的鍋被偷了。她的財產只有一口鍋,她早上去賒豆子,用鍋煮賒來的豆子,所賺的錢讓自己吃一口飯。鍋被偷了,就等于她的人生被偷了。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被別人偷走一個東西,我們的人生就沒了。如果這發生在任何一個北方國家,一定會引起非常大的關注。但它在那塊土地上隨時會發生,卻從來沒有人關注。
在塞內加爾,卡普希欽斯基遇到了一對來自蘇格蘭的年輕情侶,他們覺得和他們聊天的所有非洲人都在索要些什么,所以拒絕和任何人交流。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就是這樣產生的。但卡普希欽斯基知道,非洲人來問候你,提醒你注意安全,他認為自己已經是在關心你了,給了你珍貴的信息,應該獲得回饋、交換。這是我們難以想象的。
通過寫作,他在追求平等和尊重。《太陽的陰影》的波蘭語書名叫Heban,Heban在波蘭語中指非洲的一種木材——烏木。卡普希欽斯基在書中有一段非常動人的描述,他在聽臉上閃著烏木光澤的人講述他們的歷史,他們堅毅的臉上閃著光芒,“我不太能聽懂他們說的話,但他們的聲音是那么 的嚴肅認真。他們在說話的時候,認為自己是要對本民族的歷史負責的。他們必須將歷史完整保留并繼續發展。……每一代人都是一邊聽著別人傳授給他的版本,一邊對這個版本進行修改,不斷地改變、轉變、修訂和修飾它。但正是通過這種方式,歷史擺脫了檔案的沉重,擺脫了數據和日期的嚴格要求,歷史在這里呈現出最純粹的、如水晶般晶瑩剔透的形式——神話。”
第一財經:卡普希欽斯基這樣一位傳奇記者,他把自己的觀察留在了書里。你認為他的文本有什么特點?
毛蕊:他的作品是紀實文學,但是很難當紀實文學去讀,因為他的描寫非常生動,引人入勝,讓人身臨其境,文學性很強。但你不會懷疑內容的真實性,因為他是一名記者,他沒有夸大事實,而是用嚴謹又富有詩意的筆觸真實地呈現非洲。
全書第一句話:到處都是光線。他的波蘭語寫作讓你身臨其境,他描述了從陰霾的倫敦飛到非洲大陸,之前還是雨絲打在玻璃上,突然你就被陽光包圍了,那就是非洲該有的樣子。
這本書從“光”開始,最后也以“光”結束:“此時仍是黑夜,但是非洲最閃耀的一刻也越來越近——黎明將至。”光對于非洲是決定性的,非洲文明的很多特點、人們的生活狀態等,都和光有關。光也可能是理解這片大陸的重要鑰匙。這種把紀實與文學融為一體的寫法,是卡普希欽斯基獨一無二的魅力所在。
第一財經:卡普希欽斯基的幾本作品中,只有《太陽的陰影》是從波蘭語直接翻譯的,你覺得語言和一個民族的特點有什么內在的關聯?
毛蕊:有些作品因為出版和市場的考量,會選擇從英語轉譯,確實在速度和傳播上更快捷方便。但如果直接從波蘭語譯出,就能捕捉到一種獨特而不可替代的氣質,那就是我所理解的“波蘭精神”。
所謂“波蘭精神”,其實很難用一句話來概括。波蘭的歷史跌宕起伏,民族經歷過戰爭、分裂、壓迫與抗爭,這些痛苦和磨難塑造了他們獨特的性格——獨立、堅毅、勇敢,同時又帶著深沉的感傷。正是這樣的經歷,使波蘭文學常常帶有一種既浪漫又理想主義的底色。語言不僅僅是交流的工具,它本身也承載了歷史的記憶和民族的氣質。波蘭語的表達有時充滿詩意,有時又凝重而堅硬,這種張力其實就是波蘭民族精神的延續。卡普希欽斯基的文字中,那種對苦難的直面與對人性的深刻洞察,正是這種精神的寫照。而作為譯者,我希望中文讀者也能通過這些文字,觸摸到這種穿越歷史與語言的力量。
第一財經:最近幾年你的譯作不斷,能談談你翻譯時的狀態嗎?有沒有特別艱難的時候?
毛蕊:我翻譯一般在深夜,需要非常安靜的環境,一個人整個沉浸在文字中。讀懂的時候,就好像我一個人在享受漆黑夜空中璀璨的流星,而且它們滑動得非常緩慢,我有足夠的時間去捕捉和體會它的光輝。但作為譯者,我還要思考:如何把這份瞬間的美傳遞出去,讓讀者也能感受到?有時候我能看到那顆“流星”,卻一時找不到恰當的中文去承載它,這就是翻譯中最痛苦的時刻。但正是這種痛苦,往往也伴隨著巨大的愉悅,回想起來總是幸福的。
《太陽的陰影》的翻譯過程是比較順暢愉悅的。而我在翻譯第一部作品斯坦尼斯瓦夫·萊姆的《機器人大師》的時候,常常覺得自己面臨的是難以逾越的挑戰。萊姆的作品中有許多他自造的詞語,有人開玩笑說,可能波蘭語對萊姆太簡單了,所以他創造了很多有豐富內涵的詞匯。波蘭有一些學者是專門研究萊學的,所以在翻譯的過程中遇到這種詞匯我要去咨詢專家,還用中文體現他想表達的意義,如果沒有對應的,我就需要自己去造。
翻譯萊姆作品的過程經常像蕩情緒秋千,一開始不知道某個自造詞的含義,要去咨詢專家,冥思苦想之后終于獲得其中奧秘,好像有一種力量把我推上了理解的高峰,會有一種豁然開朗的喜悅;但當秋千從至高點回到低處時,又會感到孤獨——因為我還要思考怎樣讓讀者也能體會到這種喜悅,而不必重復我的起伏。所以翻譯對我而言,始終都是痛并快樂著。
我認為,翻譯和教育、特別人文學科的教育是一樣的,有某種“滯后性”:越是美好、越值得珍藏的東西,越是不會以直接、輕松的方式呈現。它需要經過努力、主動思索、不理解與理解,甚至受到一些挫折之后,心里才會沉淀出的一份持久的幸福感和滿足感。就像我們看到美好的景色,會想起“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它其實悄悄印在我們心里,可能在幾年甚至十幾年、幾十年之后才會回應我們,讓我們醍醐灌頂,照亮我們眼前的路。翻譯也好,文學也好,書籍也好,都是這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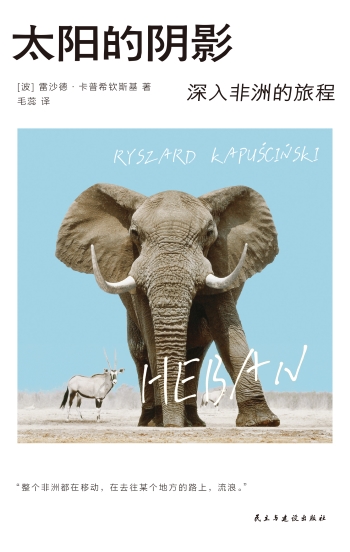
《太陽的陰影:深入非洲的旅程》
[波]雷沙德·卡普希欽斯基 著 毛蕊 譯
民主與建設出版社·理想國 2025年6月
幫企客致力于為您提供最新最全的財經資訊,想了解更多行業動態,歡迎關注本站。鄭重聲明: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文章僅為傳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標記有誤,請第一時間聯系我們修改或刪除,多謝。



